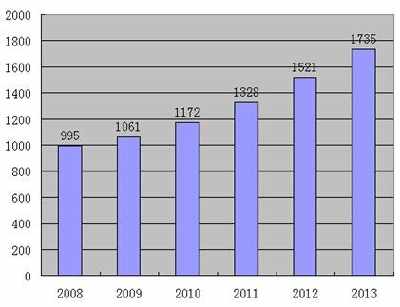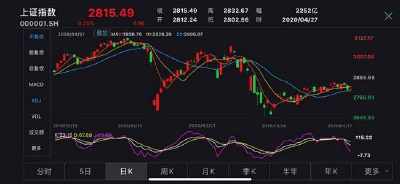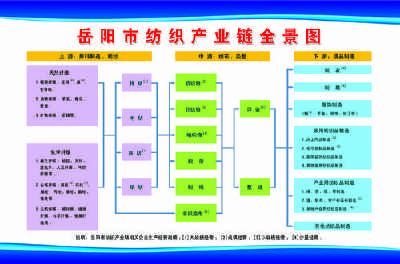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乘坐地铁并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公交车也可以用来和高速时代去菜市场的长辈一起享受乘车的轻松。你只能被迫坐地铁。9月29日,当北京13号线经过Xi二七站时,一场摔跤秀展现了地铁作为摔跤场的本质。然而,大多数时候,摔跤并没有那么激烈――你只是看着陌生人以钝角张开裤裆,就明白了哈姆雷特的那句话:“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人。”
9月初,也是在北京地铁上,我和一个把狼尾巴扎成辫子的帅哥坐在左边。我正纳闷怎么和他说话时,瞥见了他宽阔的双腿。与此同时,戴着眼镜、面容温柔的舅舅伸着下肢。
我夹在一条扎染的宽松裤腿和一条直筒裤之间,一把火砸到了我的喉咙:我给了你一个机会,因为我没有脸在裙子下面露出内衣。我提高了声音:“不知道你们两个能不能占这么大的地方?”
我故意用“你”作为礼貌。
我从来不吝啬最大的恶意去猜测公共交通中的同路人,看到一个又一个纠察队。但那天我突然想到:如果角色换了,我会不会试着翘着二郎腿坐着?
据说潮汕方言把这个叫“大郎派”,意思是生殖器太大,一定要给足空间。在Buzzfeed名为“女人想问男人问题”的视频中,女员工问道:“我们还是带着咪咪长大的。你没看见我到处张开双臂吗?”但是这个类比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的女人都怀疑她故意挑起性别对立。
既然那样坐着的人那么常见,那种坐姿里是不是隐藏着我不知道的神秘?如果我认为我占据了公共道德的制高点,我会一直欺骗自己。
改变我的习惯非常困难。第一天忘了做实验,还穿着裙子。于是我把挎包压在裤裆中间。在旁观者看来,我可能是裤裆里藏了易燃易爆危险品,也错过了安检。全身放松的情况下无法保持这个姿势:为了保持平衡,不得不在腰部用力,大腿内侧肌肉还是感觉被拉伸了。更糟糕的是脑子里有自我否定的声音,让原本的不适变本加厉:我显然不需要那样开车,现在就像有一个新的生命从我两腿之间的宇宙之谜钻向这个尘世。
实验从地铁扩展到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场合,比如首都机场的候车室。
最尴尬的时刻是我的腿连着邻居的腿,他的体温会通过他的裤腿传到我的皮肤上。感受陌生人的温暖是好的,但这种方式不太对。在回成都的飞机上,我和一对夫妇坐在隔壁。每次摸一个男生的腿,都会因为和别的男人交换歌曲而感到愧疚。我翘着二郎腿,垫着笔记本,试图记下此时此刻的不安。写完了就放开腿,趁我不备,挤过边界,妈的。
到了成都之后,为了在做社会实验和挽回面子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我想出了一些对策。首先,如果你没有脸挤进人与人之间的空座位然后劈腿,那就只能先占地盘,把挤进去的尴尬留给后面倒霉的人。于是我从繁华区坐了四五次偏僻的地方,然后回来了。对多个平台的监控捕捉到了这种令人困惑的行为。成都地铁的大部分线路上,座位上没有标明一个人位置边界的凹槽,也没有标明一个长椅上应该坐多少人。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削弱了。
一些践踏规矩的快感,但也抹去了一点政治不正确的焦虑。我还观察到,如果你刚好拉着行李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敞开腿了――毕竟万一手的握力不够,箱子自己跑了呢?我一生中从没有像这一星期一样,在等着地铁门打开的同时进入备战状态,除去在北京13号线的首站抢座位的时候。从双流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们这一侧的座位除了我,还有另一位大哥拉了行李箱,年富力强的两人岔得理直气壮,一位大叔被我们夹在中间,先是像录谈话节目怕走光的女团成员那样端庄,接着翘起了二郎腿。后来大叔提前我们一站下车了,我想暗示下大哥他这样不对,刻意坐得近了点,还在手机上搜索各种关于这个坐姿的meme,想等他无意间瞥见后开启自省。然而他打着游戏,岿然不动。我想:我是在做社会实验,那你的脸是谁给的?他下了车还站在车门前抠手机,我故意顶了他一踉跄。算是我为被我们挤到的大叔出了口气。
最后一天,我决定扔掉行李箱这块遮羞布。老子就这么坐了!滑板爱好者小周受我邀请加入了最后一天的实验。我们装作陌生人,面对面地坐着,我突然想到可以做个动漫,主角都要从胯下发出龟派气功那样的大招,应该很有趣。三四天下来,我终于能体会这样坐的快乐。真的舒服,简直胯下生风。《逍遥游》里说“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也就这么回事。身为男性的小周起初和最开始的我一样不适应,他表示平常不岔开腿也不会闷到蛋,刻意开腿令他上半身都要端着。但一个下午下来,他的身体也配合着渐入佳境。更何况我们发现,一旦你和自己和解,旁人都也会对你宽容以待。
我说我们可以带滑板,小涛说:“别,那人家就该说,滑板的人没素质。”
唯一一次危机就在近前,是当我右边的大哥直接侧过头来盯了我一眼。不过主要还是怪我:我一坐二开腿三仰面朝天,进入得粗鲁、毫无前戏。而一旦你掌握了润物细无声地得寸进尺的艺术,就会见识到儒家精神在同胞中有多根深蒂固。旁边的乘客稍微松懈一寸,我们就多进攻一寸,并且从上帝视角观赏着他们的局促:有的抠起手指侧面的老茧;本来在看小说的,仙道魔道的斗争都吸引不了他了,他几次抬头看路线图,像在期待着这场旅途快结束,但直到我们下车了,他还没到站。我们像是二十多岁还在玩小学三八线那一套的神经病,但也像是在与有着历史遗留问题的邻国争夺领土:每一步走得谨慎却坚定,不做出任何妥协。
怪不得古代帝王在画像里也都睡岔开腿的
我反思起近几年的想法和行为――我一直给合不拢腿的坐法贴上标签:这一定是深入骨髓的侵略性的外露。我甚至擅自给自己赋予地铁纪律协管员的权力。尖酸地问:“您们用得着占那么大地儿吗?”
但当我自己真这样坐了一周,才理解了他们:用不着,但真舒服。你在放松身体的同时也大可不必有心理负累: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大家心照不宣地构造着一种动态的和谐。我们试过,别担心:就算其中一个人近乎日本相扑选手在热身,原本以为已经占满的座位,还是塞得下多一个人。英语里有个词组叫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你光动用同理心是不行的,必须真的穿一下other的shoes。
最后一天的实验结束前,我右边坐了一对母女。不到五岁的小姑娘摆弄着双腿,妈妈叮嘱着:“不要这么踢啊,会踢到别人的腿,再踢我揍你。”
在春熙路下车,我告诉小涛,这是我一天中唯一内疚的时刻。
你也可以尝试下合不拢腿地坐地铁。在评论区留下或私信我们你的照片/感受,我们会为你们做一期精选,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