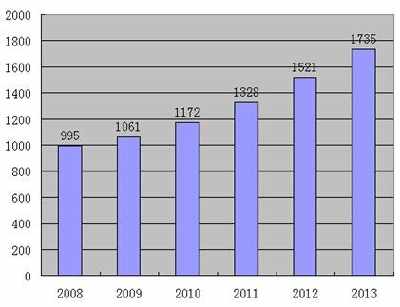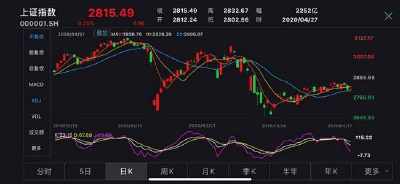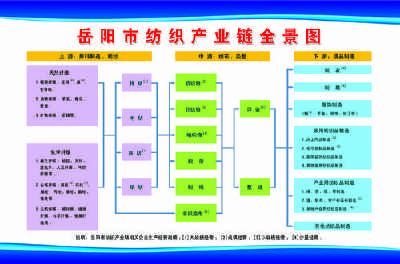本故事已由作者邱其帕独家发表,并授权其每天阅读部分故事,其附属账号“每天阅读部分故事”已被依法重新授权发表,侵权行为必须追究。
一个道士来到何谦镇,用卦解梦非常有效。当时两尺宽的卦桌上挤满了人,但老道士定了规矩。一天只有十个人,一个人只收到六个硬币。收了钱,进了街尾黄牢头的酒馆,半斤烧酒,听了一下午白姑娘弹琴。
“地方是好地方,酒是好酒,而Quer也是好Quer。不幸的是,这个何谦镇非常邪恶!”
老和尚举起杯子,用另一只手拍了拍桌子,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黄老的肚子里满是油,像六月怀胎的女人。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开玩笑说:“道士喝多了?别胡说八道。我们的何谦镇几百年来一直很安全。为什么会有恶灵?”
喝酒的人也纷纷附和闻言,只当老道士酒喝多了在胡说八道,没当回事。
白人女孩玩了《羲和》,把它收起来。喝酒的人让她出去了。老道士抻了抻棍子,拦住了白衣少女的去路。她笑着问:“这《羲和》是一百年前姑苏贵女争相学的一首歌,可惜早已成了孤儿。不知姑娘是从哪里学来这首歌的?”
白人女孩也没有生气。她回答说:“我是在闺房里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老道士还想问什么的时候,黄老头就去举起占卜杖说:“你这个老酒鬼,脾气古怪,你要阻止别的姑娘干什么?我不是你发疯的地方。”
相反,他转向白人女孩说:“快回家,夫人,不要和他说话。”
白人女孩只有一个名字,是镇上唯一的女士,五官精致。她会读和写诗,会弹钢琴和音乐。她的脾气温柔善良,在镇上很讨喜。第一天她来酒馆放音乐,黄老头给了密码。不管她是不是喝醉了,她都不应该不尊重白人女孩。否则,她会剁了手指,再也不进入何谦镇。
事情就是这样。这些年来,这个白人女孩在酒吧里过得非常顺利,攒了很多钱。她计划明年足以进京,送陈建兴进宫考试。
白衣少女走后,酒客们看着神算子老道士的眼神,又多了一层疑惑。第二天,在占卜亭前排队的人少了一半。
陈建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袍,高高的头发,腰间挂着一件雪白的玉佩,这与他轻盈朴素的服装有点格格不入。老道士目光锐利。他推开人群,冲出来扶住陈建兴,开口道:“贫贱是公子注定的,不如公子来占卜?”
陈建兴扯着袍子,想挣脱老道士的枷锁。失败后,他说:“萧声,一个学者,一直不愿意相信鬼神。道士不妨替别人数卦!”
老道士毫不留情,熟练地将陈建兴的左手翻了过来,用手指摸了摸他的骨掌。他在人行道上说:“公子出生在五子年的新游月毛毅,他生来就有逆月之福。他应该在晚年生活在高位。只有当他击中这个时,他才需要摧毁邪恶来保持他的和平!”
陈建兴对他的话嗤之以鼻,问道:“哦?道士告诉我这辈子带了什么邪灵,该灭什么邪?”
老道士捋了捋胡须,目光锐利,答道:“引恶鬼,灭恶鬼。”
这是老道士第二次在何谦镇养妖。一瞬间,围观群众一片哗然。只有陈看出他要甩袖子。他生气地说:“休是胡说。你怎么能让你那老套的妖话在光天化日之下误导人?”
老道士直盯着陈建兴的腰看着玉佩说:“年轻人不要这么固执。穷,修行多年,有妖不认错。不信就带着穷人去哟
老道士虽然半个月前才来到镇上,但他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心,对他说的话也有七八分的信任。他只看了一眼,一眼就知道了陈建兴的生日,这增加了他的可信度。因此,当你说了一句话,他包围了陈建兴,回家了。
陈家虽然穷,但是干净整洁。当所有人都来的时候,那个白人女孩正挽着袖子在井边洗菜。她听说老道士要来降妖,忙道:“既然道士觉得屋子不干净,那就赶紧练驱魔吧。”说着还端上了新茶,以示敬意。
老和尚点了点头,但没有喝茶。他咬了咬手指,在操作者身上画了一串咒语,并把它们放进了茶里。然后他点燃一支白蜡烛,折下院子里的柳枝,把茶喷在柳枝上,然后把它们轰出院子。当蜡烛烧成两半时,老和尚把柳枝举在房间里鞭打起来。
只是过了很久,屋里屋外都没有动静。蜡烛燃尽后,老和尚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
“道士,你能降服那恶灵吗?”有人忍不住问。
老道士眼神有些落寞,但还是说:“陈公子家里没发现妖怪。”
“我告诉过你……”
“如果你没有,你就没有。谢谢你们的长跑,这也能稳固我们夫妻的心。”
当白人女孩张开嘴时,陈建-杭被她拦住了。那个白人女孩脾气很好。房子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她温柔地笑了。她挽着陈建-杭的胳膊走进院子,说:“我现在要做饭了。如果道士不嫌弃,不如留下来试试老太太的手艺?”
劳道脸色有些难看,向陈家的夫人鞠了一躬,走了出去,院外的人群渐渐散去。直到这时,白衣少女才在街上见到陈:“相公不恼,道士也善良,不久就要进京了。相公只需专心读书。”
房间有点暗,白衣少女举起老和尚打翻的卷轴。墙上挂着一幅画,看起来很旧。在照片中,有一棵白色的桃树。
着红色的花,树下放着一张七弦琴,画工很好却总觉得有些单调。而那画上方才被老道士挥柳枝打过的地方却隐隐渗出些红色来,细看之下却更像血迹,白姑娘抬手将画取下,衣袖滑落时,那白净的手臂上竟有条红色的鞭痕,皮开肉绽地格外惹眼。
老道士夸下海口说要降妖却无功而返的消息不胫而走,霎时间,整个千河镇茶余饭后都将之当做笑话来说嘴,而去找他算卦的人也只当是算个乐子,那门可罗雀的卦摊如今倒是清冷了起来。
只是这老道士却疯魔了般,白天守着那卦摊,傍晚时候便拿着个罗盘围着千河镇一圈圈地走,甚至还在陈见行家门外贴了符,也亏得白姑娘好脾气不与他计较,拦着几次想与他理论的陈见行。
可是有一天,老道士却在黄老头的酒馆举着桃木剑指着白姑娘,大声呵道:“你这画妖,还不快快现形!”
可是白姑娘怎么会是妖呢,妖都是凶面獠牙,杀人喝血的怪物,白姑娘从来和善,样貌又动人,和妖这个字可不沾边呀!
酒馆里的人只觉这老道士想抓妖想疯了,为了那二两功德竟然要平白污蔑人家白姑娘。
黄老头是个急性子,身子笨重动作却快,拿了个算盘便想要将那桃木剑挑去,可这次老道士却发了功,凭借着一身的修为本事站在白姑娘面前纹丝不动。
“尔等凡夫休要误我降妖,若不快快除去这妖孽,整个千河镇可都要遭她迫害!”
桃木剑挥起,挑过白姑娘的衣衫,白姑娘踉跄躲闪,却撞上了身后的酒桌桃木剑再次刺来,只是那剑抵在她胸前却再无法伤她分毫。
“怎会......”老道士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剑,又抬眼看向白姑娘,似乎很想从她毫无波澜的眼中看出些什么来。
只可惜,白姑娘冷静得可怕,扶着那桌子站起来,理了理衣裙,有些委屈地问:“可是芫娘何处得罪了道长,惹道长几次三番为难芫娘?”
酒馆里的人们也忍不住对着老道士指指点点起来,他却置若罔闻,更加坚定地将剑抬了抬,道:“画妖怕火,若你当真不是画妖,用火一试便知!”
“画妖怕火,那人便不怕了吗?道长是想降妖还是想娶我性命?”
老道士来不及解释,便被黄老头招呼着酒客们哄出了千河镇,还告诫他这辈子再不许踏入千河镇。
陈见行是半个时辰后来接白姑娘回家的,一路上义愤填膺,恨不得追出千河镇去踢他两脚才算解气。
只是这老道士才离开千河镇没几天,这镇子上便出现了怪事,镇上有一口百年老井,供了几代人的喝水,可有天清晨,镇民前去挑水,那水井上却长满了带刺的藤条,彷佛一夜之间,这井便荒废了。
有人拿火去烧,第二日那藤条却又长了起来,甚至镇上别处的水井都长出了藤条,只是没有这般密集,藤条越来越多却无人能治管,这时有人想起了老道士,也想起了他说这千河镇妖气甚重之言。
四更天,家家熟睡,只有低微的犬吠身,白姑娘穿了身黑衣,头上还戴着斗篷,蹑手蹑脚地往老井的方向走去。
藤条有了灵性,在夜色下摇曳起舞,偷偷吸食这天地的灵气,却在看见白姑娘的那一刻收起了飞舞的枝桠,悄无声息地彷佛死物。
白姑娘用匕首划破手掌,将血淬在匕首上,两三个飞步间就扎向中间最粗的那根藤条,可那藤条似是垂死挣扎,舞着自己的枝桠便想将白姑娘锁住,只可惜白姑娘身手敏捷,只留下几个残影,便躲开了藤条的攻击。
未几,藤条油尽灯枯,终是化成了一段段枯枝,风一吹便消散在了夜色下。
白姑娘还未来得及放松下来,身后却突然袭来一阵掌风,随后便是桃木剑急攻厉下,白姑娘连连躲避,却被逼在墙角,再无还手之力。
“贫道早就说过,你留在千河镇迟早会给他们带来灾祸的。”老道士义正言辞,眼神也未有丝毫的犹疑。
“我从来没想过害人。”白姑娘脸色有色发白,方才对付那藤精废了不小的功夫,实在是应付不来突然出现的老道士。
“你虽没有害人之心,却有精怪妖鬼循着你的气息来害这一方的百姓,只可惜他们想错了,身为同类的你却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我跟他们才不是同类,我不是妖,我只是想好好陪在公子身边......”
“人妖殊途,人鬼也殊途,我虽看不清你的真面目,却知晓,你并非是人,你虽能化作人的模样在陈公子身边,却不能为他生儿育女,更不能陪他颐养天年,等他百年之后,你还是这般年轻女子样,你还觉得你们这样的一生是值得的吗?”
老道士不懂情爱,一双眼睛里满是道义,他的道是斩妖除魔,他的义是造福苍生,他攒着这降妖救民的功德,为的也是修行数年能得道飞升罢了。
白姑娘并不肖老道之言,趁着老道士不注意,反手将匕首挥向道士颈间,可老道士眼尖,侧身躲过后,一掌打在白姑娘肩上,白姑娘趁机挣脱了束缚,老道士运着内力将桃木剑往前推出去,狠狠地扎在白姑娘后背上,那冲劲力道虽将白姑娘打得一个踉跄,却还是让她消失在了夜幕中。
白姑娘消失了。
陈见行次日清晨出门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有人看见白姑娘,通红着眼眶,惨白着脸,就这般浑浑噩噩着找了白姑娘一日,却连白姑娘的踪影也不见。
老井里的藤条没了,有人说白姑娘是叫这藤条给吃了,陈见行竟攀着井边就要往里跳,幸而身边的人手快将他拉住了,才没叫他成为这井里的亡命人。
可白姑娘终究还是不见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老道士出现在陈家的院子里,手里还拿着幅古画。
陈见行有些失去理智,冲上去便捏住老道士的衣襟,质问道:“你这满口胡言的老道士,是不是你害了芫娘,你将芫娘还给我。”
老道士难得沉稳,任凭陈见行这个文弱书生将自己衣襟抓着,手中却展开了古画,问他:“陈公子莫急,公子可认得这幅画?”
陈见行粗略地看了一眼,哼道:“当然认得,这是芫娘家传的名画,怎会在你手里?”
“难道陈公子就没发现这画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画会有什么不同?陈见行不解,却还是松开了手,去端详那幅画。
画确实变了,当初那白桃树下单单放着一把七弦琴,如今,那树下的分明是位弹琴的妙龄女子,而那女子的五官相貌,跟白姑娘一模一样。
陈见行又惊又奇,连着揉了两次眼睛,生怕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又是一杯茶水,一张符咒,一根柳枝,老道士却只念着咒抽打着这幅古画,未几,那画中竟掉出个伤重的女子来,而原本画中的少女,也随之消失不见。
有围观者吓得四下奔走,陈见行却扑上去,将女子小心翼翼地抱入怀中,喊着:“芫娘,芫娘,你可还好?”
姑苏城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可白家最出名的是那位刚刚及笄的大小姐白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特别是那一首七弦琴弹得动人心弦,绕梁三日,余音难绝,甚至自己写了首曲子叫做《羲和》,一时间成了姑苏贵女争相学奏之曲。
白家主君是个商人,自己肚子里没多少墨水,却十分喜欢附庸风雅,一有空便在家中办雅集,请的都是些文人墨客,曲水流觞吟诗作对,无论是谁作了诗,都会跟跟叫一句好,因此他家的雅集也格外热闹。
白芫与方知误便是在雅集上相识的,方知误诗词不精,却作的一手好画,别人吟诗,他便在一旁描摹丹青,有花有水有文人有贵宾,还有一幅美人图。
一幅白芫坐在白桃树下弹琴的美人图。
院子里有溪水流淌,白芫站在这边,方知误站在那边,他拿着画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对她说:“白姑娘,方某不才,对不出姑娘的下联,便作了这幅画当作赔礼,还望姑娘不弃。”
白芫很喜欢方知误唤她白姑娘,别人见她总是小姐小姐的唤着,显得她高高在上好不自在,还是唤姑娘好听,像百灵鸟的叫声。
画是丫鬟接过来的,白芫展开来一看,又惊又喜,她是头一次看见自己弹琴的样子,又专注又动人,这画她很是喜欢。
既然收了别人的礼物,那她也该要回礼才是,于是她解下了腰间雪白的银浆玉佩,递给方知误道:“这画我喜欢,这玉佩当是回礼,你不许不收,以后多给我画些画。”
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回熟络了起来,雅集时就在后院的溪边见面,只要有两三日不得见,白芫心里就难受得厉害,只能拿出那幅画来睹物思人。
本该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成就一番佳话,只是造化总是弄人的,白父要给白芫说亲了,说的亲却不是这些个他喜欢的文人墨客,而是与他生意上往来最盛的慕容家。
白芫头一次跟父亲闹了脾气,说自己死也不嫁慕容蛰,父亲骂她:“你若不嫁便去死吧!”
转头,白芫就回了房间将自己关起来不吃也不喝,直到父亲将那块染了血的银浆玉佩扔在她面前,跟她说:“你不就是想嫁给方知误吗?现在他死了你也嫁不成了,乖乖去做慕容家的新妇吧!”
晴天霹雳般,白芫胸口一疼,只觉眼前发昏,握着玉佩直直就倒在了地上。
她没能将自己饿死,两三个老嬷嬷摁着她一碗一碗的白粥灌下去,没个两三天就将她从病态模样变回了面色姣好的大小姐。
半月后,白芫腰间戴着白玉佩,怀中抱着那幅画,身上穿了鲜红的喜服,坐上了慕容家来接她的花轿。
她的心上人死了,她却不得不做上仇人的花轿去跟仇人拜堂成亲,心中悔恨交加,怨念横生,而唯有殉情,方能告慰那因她而死的心上人。
新婚夜里,外边的喜宴热闹非凡,屋里的新娘却握着把匕首自刎在了新房里。
心上人死后,她被迫坐上仇人的花轿拜堂,大婚夜自刎在新房
那日,姑苏下了好大的雨,雷声轰鸣,一道雷降在了白家白芫闺中的房间,一道雷落在了慕容家的祠堂。
只因他们一个逼女联姻只谋利益不顾子女死活,一个丧尽天良为了娶亲而对文弱画师痛下杀手。
一个善画的儿郎曾在夜里被五六个黑衣人围堵在白府外,一连刺了数刀,至死都想着要是能再见到他爱的姑娘就好了。
一个善琴的姑娘在她新婚的夜里,为了不辜负那场无疾而终的爱自刎房中,只想着若有来世一定一定不要负了他。
而那个夜里,却有个姑娘抱着幅画拿着块玉佩,想找到她的心上人。
有画成妖,亦有画中人成灵。
白姑娘就是画灵,是白芫的执念化作的画灵,她将自己当作白芫,心中只有一件事,找到方公子,长长久久地陪伴他,再也不辜负他。
白姑娘寻了百年,寻到了方知误的转世陈见行。
初见时她追着他道:“公子不记得我了吗,我是白姑娘啊,我找了你这么久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白姑娘一副好相貌,眼睛干净得一点都不像是个骗子,陈见行问她家在何处可有亲人,白姑娘却一概不知,只说自己叫白芫,一直在等他。
陈见行不忍将她一个姑娘家扔在外头,便捡了她回家,日久生情,竟成了夫妻。
老道士也终于明白了过来,为何自己察觉陈家有异,也推测出白姑娘并不是人,却拿降妖那套术法对她毫无作用,因为她本就是这超脱六界的灵物,什么妖精鬼怪的伤不了她,自己的桃木剑降妖咒也奈她不得。
可终究,由观世音撒于这天地间的柳枝起了作用,白姑娘虽躲回了画中,却依旧被老道士用柳枝逼出了真身。
百姓们理解不了什么是灵,只知道那个和善美丽的白姑娘原来真的不是人,纷纷提议着:“烧死她,烧死她!”
就好像当初处处维护她的不是他们一般,尽管她从未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他们的事。
而站在她身边的,亦只剩下陈见行,他将她护在身后,解释着:“芫娘不是坏人,芫娘不是妖,芫娘不会害你们的。”
而那群镇民却道:“陈公子,你是读书人,可莫要被这妖精迷了心智啊!”
一人呼万人应,老道士也对陈见行道:“她因念而生,离于万物法则之外,本就不该存于世间,陈公子,还是让贫道送她去到她该去的地方吧!”
老道士举起柳枝,注入符咒,抬手就要挥向白姑娘,陈见行侧身,将白姑娘牢牢地护在怀中,下一刹,两人竟齐齐消失在了院子里。
竹林里,白姑娘奄奄一息,她耗尽了灵力,将两人带离了千河镇,风一吹,竹叶沙沙作响,陈见行抱着白姑娘,眼泪止不住的滑落。
“芫娘,你别离开我,我不管你是什么,你都是我的娘子,我只要你在我身边。”
白姑娘抬手,将他的眼泪拭去,喃喃道:“小姐,这一世我没有辜负公子。”
陈见行不知其意,却看着白姑娘脸色一分分白下去,只得将她抱得更紧了些。
见他这般,白姑娘笑道:“相公,画灵死了是不会有尸首的,你一定要选件好看的衣服给我做衣冠冢啊!”
陈见行佯怒道:“再胡说就不给你买新衣服了。”
白姑娘歪了歪头,道:“不买就不买,反正也穿不到了。”
“相公,我那件蓝色的纱裙就别买了吧,太好看了我舍不得。”
“好。”
“那我死了你一定要给我烧纸钱。”
“嗯。”
......
“芫娘......芫娘?......其实我早就猜到你不是人了,你没有脉搏呼吸很慢,我也曾害怕地想跑掉的.....可是我太喜欢看你笑了,你笑得真好看啊......”
“芫娘,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和你做夫妻。”
“我也想的,相公。”闭了眼睛许久的白姑娘突然睁眼道。
陈见行苦笑一声,道:“这时候了竟还逗我。”
“不逗你了相公,你好好活着,我会在画里一直陪着你。”
“好。”
“那你一定多给我烧点纸钱。”
“好。”
怀中的温软一点点消失,直到连模糊的轮廓也逐渐消散,陈见行终于不再强颜欢笑,一遍遍叫着芫娘,竟惊起一片飞鸟。
星子散落,陈见行回到家中,那幅画里没有少女,白姑娘逝了,不在世间,也不在画里。
只有陈见行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回来,会重新出现在画里,然后从画里跳出来,唤他:“相公,我回来了。”
白姑娘其实一直都明白,她不是白芫,陈见行也不是方知误,可她的执念在遇到了陈见行后,就从方公子变成了陈公子。
这一世的陈见行和上一世一点都不一样,他清冷不爱多言,方知误善谈却腼腆,虽然长着同一张脸却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而她对陈见行的感情,早就不是白芫对方知误的悔和念,而是彻彻底底的情深不负。
次年,陈见行入京赶考,一举夺魁成了状元郎,面对皇帝陛下的赐婚,他却以家有娇妻为由拒了赐婚,只是,直到他搬入新宅,朝中都无人见过他的妻子,被人问起时,他指了指那幅画。
画里有颗白桃树,树下有个弹琴的少女,而少女边上,站着位目不转睛看着她的少年郎。
只那少年啊,似是有人添了笔,新作上去的。(原标题:《芫娘》)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