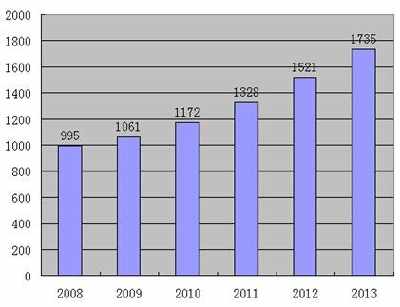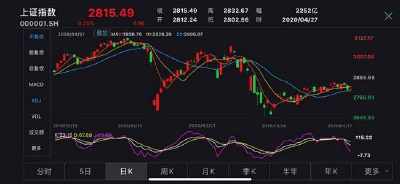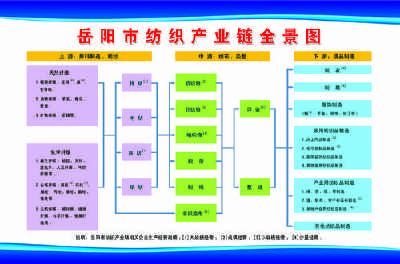正文:红九
图片:来自互联网
这篇文章已被作者授权发表。
姐姐已经上学了,我要一个人在房子前后徘徊。有一天,我二姨家的二表哥退休当了几年工程师,已经安排好了回县邮电局的工作。在回到家乡之前,他来南京看望我的父母、他的叔叔和罗伊。我们沛县的老家叫我阿姨“金子”,这个名字很奇怪。
我的二表哥王春友,身高1.8米,颧骨高,脸型大方,皮肤黝黑。他棱角分明的脸就像拿着刀和斧头的石头。他说话声音很大,当他笑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以震碎屋顶的瓦片。他也爱笑,笑的时候总是夹杂着大声咳嗽的声音。简而言之,我们家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他的体形和声音。
不知道怎么讨论。父母决定让二表哥带我回老家。先带我去爷爷奶奶家,然后他会回二姨家。
如果你说走,那晚上就和二表哥一起坐火车去徐州,然后坐火车转车去沛县。记得那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我站在火车站门口等火车,二表哥正和几个老乡有说有笑。突然失去了出门的兴奋,感觉有点孤单,有点想家。
过了一会,二表哥从什么地方买了一包熟菱角给我。这菱角是一种有六个尖顶的野生小菱角。它的壳很硬,但它的肉又硬又甜。一路上,我津津有味地品味着老凌,用手采摘,用牙齿咬地,消磨着老凌和时间。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我已经在爷爷奶奶家了。坐在爷爷奶奶抽烟的锅屋(厨房)里,又窄又黑,堆满了柴火,只点了一盏豆油灯,我有点害怕和不安。奶奶轻声对我说话,我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更紧张了。
爷爷一句话也没说,抽着烟,却低着头,用小棍子在又脏又黑的锅灰里扒拉几个同样黑的东西。奶奶指着小木桌子上的几个菜和一篮馒头,让我吃。我摇摇头,没有任何味道。然后奶奶一直问爷爷还好吗?我看到爷爷选了一个那种黑色的东西,在上面打了几下黑灰,就开始脱皮了。突然,金黄色、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红薯神奇地出现了。
我咬了一口。太甜了,太香了,太辣了。好像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被拉长了,全身都暖暖的。之后,我觉得锅灰不再脏了。烤馒头、红薯、煎饼和埋在锅灰里的花生成了我的最爱。
我分散的农村生活正式开始了。
首先,我不再孤独,像一个仙女坠入凡间,受到身边亲人的称赞和关心。我爷爷和哥哥四岁,他是第三个。他们是李家的“法”辈,曾祖父裸替四个儿子取名“金银财宝”,不改色不跳,所以我从来不羞于说出祖父的名字——“李发才”。
曾祖父在农民家庭中相对富裕,留下四个儿子,有一所大房子,从东到西,按辈分顺序居住。祖父在一个欢乐的场合结婚了。他患有肺结核。他结婚没几天就走了,留下最穷的曾祖母做了一辈子寡妇。
奶奶收养了四爷的孙子,所以表姐和奶奶住在最东边的房子里。我还记得那个有点重听的曾祖母,总是怯生生地笑。她和人打招呼时不怎么说话。她静静地站在旁边或坐在旁边,没有多说什么。她有一双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睛,窄窄的鹅蛋脸,非常精致漂亮。
收养她的表姐对她不太孝顺,对她颐指气使。曾祖母家的右边是二奶奶家,里面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她还收养了四爷爷的孙子。右边的二奶奶家是我爷爷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爷爷奶奶都不顾一切要生我爸爸的原因,不然四爷爷家的孙子们就活不下去了。
最西边是四爷家。他家的孩子虽然和爷爷家的孩子数量相当,但是相差很远,因为他们有六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而爷爷家是七个女儿倒水出来。
到了吃饭的时间,我总是喜欢端着碗,跑出房门,从一个屋子游荡到另一个屋子。结果,这家人吃了几口蔬菜,那家人啃了几口馒头,撕了半个煎饼。阿姨们热情地迎接我,从柜子里翻出藏起来的桃子蛋糕和饼干,舍不得吃,偷偷塞给我,让表兄弟们看不见。没有这些高档食物,阿姨们会放很多糖,给我倒一杯白糖水。
我的阿姨们也每隔一段时间来外婆家做客,总是会带一些好东西:一刀肉,几条鲜鱼,还有稀稀拉拉的新米饭。我的家乡几乎没有种植水稻,主要是面食,只有古琦一家种植一点水稻,所以每次古琦都会带来一些新的水稻。
阿姨们看到我冬天穿的棉袄又小又破。他们商量着给我买了棉布和棉花,还缝了一件又大又厚的棉袄。这件棉袄我穿了好几年了。
每天,一大群表兄弟带我去玩,在田野里,在树林里,在荒野里。我们捡树枝,耙树叶,带回家生火;挖鸟窝,捉麻雀,烤;摘果打酸枣;到处收集头发和彩纸,找一个卖糖果的拨浪鼓小贩。我们也一起工作。
记得我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我们家的孩子摘棉花桃子。棉花桃上的刺又尖又小,而且棉花桃的壳又硬,不小心就会刺。
痛了双手。把棉球摘下来后,我们就挑捡干净,再撕开,扯成大大的,松散的棉花。然后休息时,我们就躺在白花花的棉花里,晒着暖暖的太阳,好舒服。我更学会了野地里用小木棍揩屁股,刮几下了事。
爸爸时不时地寄钱、寄食物给爷爷奶奶。每到有汇款单来时,爷爷,奶奶就非常高兴,带上我,赶一大早,走很远的路,到镇上的邮局去取钱。到了镇上,爷爷先安排我和奶奶在早点店坐好,歇歇,等他去取钱。爷爷取了钱,我们就像过节似的大吃大喝一顿。其实也就吃些油条,油饼,饺子什么的,这些就是我们当时的大餐了。
吃饱喝足,爷爷就领我们赶集。有一次,爷爷领着我,走到一个卖花生的老头摊前,买了把花生,包在纸里,给我吃。我一看,这花生有点湿,普普通通的,就像生花生,好吃吗?尝了一个,才知道,这花生,是那么的咸香软糯,清香新鲜中还留有泥土的气息,原来是咸花生。自此,我一直念念不忘咸花生。
逢红白喜事,就有最开心的事情—吃大席。每次都是奶奶带着我一起吃。大席的菜无非就是些凉菜,热菜,再加汤。我记得那时,我最爱吃的凉菜是凉拌蒜蓉海带丝。
奶奶一上来先给我夹很多海带丝,我就慢慢地,一根根地吃掉。那时候,村里的人家还都很穷,大席上,整鱼,整鸡,整鸭什么的大菜根本没有。吃的最多的是酥菜:什么酥山药,酥土豆,酥萝卜丸子,最高级的是酥小鱼。
酥菜就是用混了香料的面粉裹上菜油炸,吃时再烩上粉条,豆腐,大白菜,菠菜,等等,热气腾腾地一碗碗,香气扑鼻。每当菜一上来,大家就一抢而空,连菜汤都用馒头蘸得干干净净,一滴都不剩。
最后的一道汤,叫羹汤,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的,最美味的汤。一般主人家会杀一到两只老母鸡,就是为了熬羹汤。其实羹汤就是鸡丝酸辣汤,但没放辣椒粉,只放大量的白胡椒粉。
汤里面有撕得一丝丝的鸡丝,嫩嫩的豆腐丝,黄花菜,海带丝,木耳丝,蛋皮丝,等等,再勾芡,滴上自家磨的麻油,醋,又烫又香又麻又酸,无比的美味和畅快。毎次,只要羹汤一端上起,大家就轮流端起碗,对着碗边,一人滋溜一大口,再传给下一个人,谁也不嫌谁脏,直到喝得底朝天,喝的个个满头大汗,酣畅淋漓。
大席结束了,爷爷喝得微醺醺的,我也吃得肚儿圆,坐在大车上,一摇三晃地,回家了。
一晃,下放农村已经半年,爸爸来接我时,看到那个一头虱子、上身敞着棉衣、下身腰间用一老太太宽带胡乱扎着肥棉裤、手捧一大海碗呼啦呼啦喝糊糊的满脸黑灰的我,楞了半晌,呀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