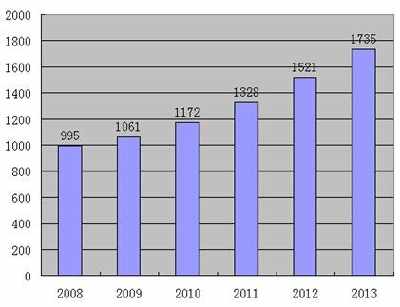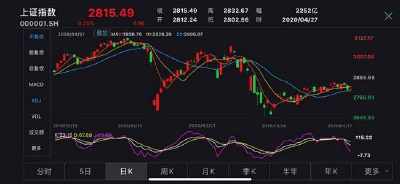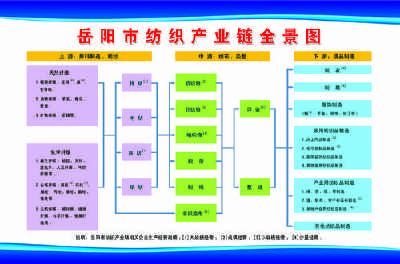作者于
宫本辉被称为日本民族作家。但在国内,东野圭吾远不如村上春树出名。一方面,翻译作品介绍不全面;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作家以无声的风格写作。几乎没有什么大浪,大事件,大悬念。它总是不冷不热,持久,缓慢而简单。独生子女本慧宫古出生于战后,曾被嘲笑为“可怜的少爷”他父亲去世时他22岁。母亲吃了安眠药,企图自杀。25岁时,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对疾病产生了恐惧。结婚生子,苦苦挣扎,辞掉工作,立志做小说家。对获得文学奖的痴迷与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非常相似。
龚本辉,1947年出生。毕业于寿门学院文学系。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后来辞职专门从事创作。1978年,他凭借处女作《泥河》获得太宰治奖,次年又凭借《萤川》获得芥川奖。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连续剧和舞台剧。代表作品有《泥河萤川道顿堀川》、《锦绣》、《幻之光》、《月光之东》、《避暑地之猫》、《梦见街》、《优骏》、《流转之海》等。
他的代表作品大多暗示自我写作是为了治愈创伤。亲子关系是它最关心的主题。0301001《约定之冬》先后获得太宰治奖和芥川奖。这奠定了宫本辉文学的基调——从家族父子出发,着眼于成长,以生死为目标。《泥河》中的哲学也是年轻作家的投射。——贫穷和孤独,阴郁和悲伤。父亲事业失败后,他去找女人辞退了他,死后留下了一笔债务。小说《萤川》既是延续,也是补偿性的“对仗”。在故事的调性上,也淡化了阴郁,使之越来越清晰。小说中,虽然郭俊失去了亲生父亲,但桂二郎对他的照顾比父母还要多。圭二郎的妻子去世了,但她不想再找别的女人。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对员工负责,就像刘美子给人的第一印象一样:坚持不懈和骄傲。理想的父亲显然满足了作家的潜意识需求。
《春梦》,作者:(日本)龚本辉,译者:刘子君,版本:北京时报中文出版社,2021年1月。
1平铺直叙,也有迷人力量
《约定之冬》的标题让人想起了《关于冬天》这首歌。也许,约,是协议的潜台词。换句话说,这个协议是在考验信仰。相信未来,还是只相信现在,是一种人生观的追问。龚本辉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浪漫,也有理想主义的现实。约定的冬天不是即将到来的冬天,而是“冬日里温暖的阳光”。写的是“小运气”,真的是生活的安定和艰难。没有对抗冲突,没有戏剧化处理,甚至连剧情都迷失在日常细节中。这样的小说怎么写?答案是,照原样写。慢慢地,慢慢地,漫不经心地,生活的节奏是作家最好的老师。
这部小说就像两个家庭住在一起。贾冰和上原十年前成为邻居。看到冰六妹子的父亲死于意外,母女俩搬走了。十年后,我又搬到了这里。前吉次郎的妻子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远离工作和学校。长子郭俊是他妻子和前夫的遗腹子。郭俊自己的祖父苏多润苏克想念他的孙子,上原的老师对老人表示同情,所以郭俊定期去看望他。小说以诸多约定为线索,像一张交织着人物的河网。十年后美代子莫名其妙地收到了的求婚,上原的老师受须藤老人的委托,履行了方的赔偿协议。弟弟梁答应父亲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留在美代子与同学团聚,并捐款建学校.因此,他们实现了小说时间和空间的极大扩展,混合了过去和未来的时态,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对话,以及一个寻找失落的循环。履行合同的过程就是人生的完成,是同步的,也是重叠的。
协议不仅仅是小说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叙事的结构性力量,即框架、坐标、语境和模式。换句话说,《约定之冬》的成交量是由一系列问题决定的,比如合同数量、合同如何运作、如何履行合同。龚本辉用这么普通的题材写这么长的故事,风险可见一斑。然而,他巧妙地利用约定的铺垫性质,埋下了电缆的布局,最终将电缆连接到榫上。
在大多数小说中,认同并不被视为一种建设性因素,相反,它往往作为一种颠覆和摧毁的因素出现。例如,违反合同往往会带来崩溃、冲突和幻灭。可以说,80%以上的悲剧都与违约有关。因为它能带来很多集群效应,连锁反应——如欺骗、背叛、抛弃、报复.这样就激化了故事的矛盾和驱动因素,很容易解决。但是宫本辉要写业绩,要从“顺周期”的角度写,这是写平淡的挑战。这部小说类似于开篇,告诉你凶手是谁,主动抛弃悬疑思路,直接分析过程动机。
这就是自信,相信单纯依靠平淡的故事也有迷人的力量。我们也可以试着弄清楚作者的意图,积极写表演也是好的。在我看来,它的本质是一种“限制性写作”。协议本身就是一个确定性的元素,可以调节故事的走向和动态,以及人物的交织形式。戴着镣铐跳舞,从反面理解,是一种一定的自由。无限的可能性有时会混淆故事和作家。龚本辉明白,每一份协议都是未来时态,都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预言,都是掌控生命的力量。
《约定之冬》,作者:(日本)龚本辉,译者:声誉,版本:99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2无常与悲哀,才是人物的大敌
龚本辉似乎没有刻意操作,但却包含了——滤镜类型、灯光和暖色处理的独特逻辑。可以说,小说完全构思了一套人生理想。
,人情模态和伦理范式。这些大多充满寄寓式,甚至有成人童话的影子。所写人物,大多是“正向情感系”:不是君子美德,就是明丽女子;不是信义当头,就是情深不已。很难发觉其中的“负向性元素”(那些破坏力、阻力或恶意),要么鲜有,或被遗忘。作家有意取消了人为冲突,对抗矛盾,将其让位给自然(岁月、疾病、死亡)。无常与悲哀,才是人物的大敌。巧合,则给平稳静默故事略添微澜。细看文本,会发现看似“老实的现实主义”,也暗藏作家许多机心。留美子在收到少年俊国情书后次日,父亲就意外身亡。这个求婚之约,既莫名荒诞,又很不吉利。时间点的接续,无疑是隐喻:俊国出现,如同对父亲的接替,它类似婚礼上一个岳父把女儿交给女婿的符号意义。在家庭结构上,强烈的互文与对称感,也颇具意味。留美子母亲寡居,俊国继父丧偶;留美子与俊国,都没了生父。甚至,上原与须藤,同是鳏夫,这组忘年之交,因孤独更融洽。
身世相似相通,处境共情理解,是小说内在大逻辑。宫本辉也许为了情感结构的均衡,补差,与轮动,如此设计。同时,这也对叙事形成奠基。小说正是不同情感角色,伦理关系的嵌合与并置。它几乎囊括各类亲缘、社群身份——姐弟、母女、父子、同学、同僚、邻里。这些关系,构成生活世界。各种场景逐幕切换,显示作家对细节浸润之深,写实的扎实功力。留美子对弟弟的照顾,与母亲的日常讨论,对佐岛老人的救助;上原先生对须藤老人的慰藉,俊国对留美子克制又大胆,羞怯且忧虑的爱慕,皆以生活场景,靠对话行动,呈现流出。
《幻之光》,作者:(日)宫本辉,译者:林青华,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3.细节并不等于琐碎的无意义
让场景自己叙事,靠对话表达价值,这属于活的现实主义。没有大量介入式评论,外部给定式描写,也没有流于自然主义平浅的浮光掠影。细节,并不等于琐碎的无意义,而是富于态度,蕴藉情感。宫本辉看似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实质上有他的取舍和考量。他意欲实现某种净化,将人情美,自然美与风物美高度提纯。这倒让人想起沈从文来,同样的无事淡淡伤,同样的清冽之美。不同的是,《约定之冬》在情绪面之外,探讨理性、原则对人生实现的塑造。如何独立使用理性,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这个康德式命题放于小说人物上,也很切题。
道德原则,义理规范和自我检视,促使人物精神成熟,情感深化。留美子反思自己儿时爱爽约,如今又遗忘同学小卷的约定。在经历一个失信男人的情感伤害后,她更觉得约定可贵。少年芳之在毁坏名表后,得到女主人宽大谅解,励志日后挣钱赔偿。从这一角度看,作品有成长小说的维度,心灵成长是隐而不发的结构力线。
《春梦》中,哲之梦里的蜥蜴,隐喻生死同构,周而复始。蜥蜴是触发哲思的引题。当蜥蜴被钉在柱子上,不能动弹。这钉子是否该拔,到底是选自由地死,还是失能地活。与其相似,《约定之冬》中,“飞天蜘蛛”也成了贯穿小说的核心意象。宫本辉不厌其烦描写蜘蛛的品种,考证如何去飞,看似反复累赘,实则是破题统摄的关键。“迎雪”的别称,意味蜘蛛的守时,可为物候。其借助气流温度,风向条件,虽不知远近生死,归于何方,但依然冒险一搏。大有破除万难,也要赴约的志气。蛛丝绕结易断,也说明约定难守易逝的现实。
意象隐喻,既是一种道具设计,主题楔引,也为叙事造境。宫本辉虽是古雅的日式抒情承继者,又不愿限于传统幽玄、物哀、景气等美学范畴。他属于那类表述人生论,价值论,探讨生活美学的作家。如弟弟亮所言,原木要等五六十年,方可入料,去做家具。愿意等待守候,功成不必在我,本就是一种“日本名人”的态度。宫本辉的叙事境界,也与之契合。不在乎故事短线的悬念刺激,不追求人物矛盾的震荡冲突。他看重长线的情绪释放,情感累积。
只有从这种角度理解,才能阐释守约的逻辑与可能。它绝非单纯的理想化。小说中诸多闲笔,粗看絮叨重复,停顿逗留,横生枝蔓。然而,作家也许有自己的道理。上原挑选雪茄,品鉴产地、品牌、气味,精确到每次吸食的长度比例,犹如帝王在决定临幸妃嫔。留美子父亲对木头痴迷,搜集各式旧木料改装房间。这些都是耐性,消磨而成的癖好。它也许在暗示,守约之人的特质:有癖方情深,恋旧才重义。
《泥河·萤川》,作者:(日本)宫本辉,译者:袁美范,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4月
4.保有日常化的审美耐心
作家遇人就写原委来历,逢景就写地理风貌。无论是帮佣、司机,还是寿司店老板娘,都会牵引几段家庭过往。这倒是一种小说里的“平权”:即使闪过的人物,也没有沦为符号。而他对空间地理的迷恋,对日常的审美品鉴,都在那些随笔式的速写中,得到运化。以至于居所庭院,山川乡野,茶饮温泉,无不显示生活美学。不妨以“家常小说”形容这种写作。所谓日本式抒情,本质在于保有日常化的审美耐心,挖掘平淡中的“习惯性力量”。无意识的反射,可能是无聊烦琐的,但也是熟悉舒适的安稳。既然有小说迷恋冲突,强化节奏;那么,也会有作品走向另一端——“拉家常”,写情绪,遗忘节奏。
《约定之冬》对节奏近乎原生态的处理,使600余页的叙事时间,尽可能贴近现实的漫长。它造成心理体验的延宕,正如一部影片的播放速度(倍速,常速还是慢速)决定了感官效应。但宫本辉又有奇特处,长镜头般的日常纪事,读来却可以很快,很轻盈。究其原因,在于小说连续性好,惯性强,状态松弛。就像那些“昭和美人”的观感,亲切温软,能快速拉近心理距离。
小说常有几类“大部头”:一种是广度恢宏,恨不得装下整个人间、时代(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一种是意识流动,耽于内部的心理现实(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约定之冬》也许属于另一种,漫长的“生活流”,不绝的情感流。它淡且稀松,是泡发后的松软。每个板块都松动,每个细节都寻常。但当它显出全景时,却平易得百感交集。那是深潜人生的蓦然、温润,恒久的凝练情感。宫本辉试图找寻人性里的恒久不易。约定,即是抵抗侵蚀,遗忘的可能。“别忘了生活”,或许是小说的教谕。《约定之冬》以温存默会的情感态度,写人生遮蔽的本质,不易察觉的恒常,如同一声温柔叹息。
撰文|俞耕耘
编辑|张进
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