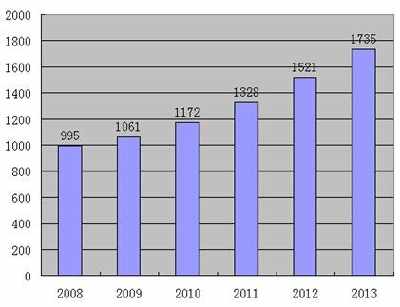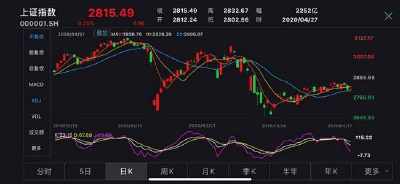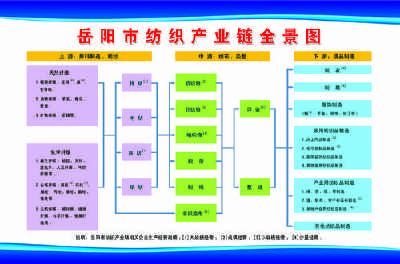邱小龙(姜立东画报)
正如邱小龙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一个非常书生气和“有点迂腐”的上海人。出国多年,本地口音没变,说话总带点上海口音。他笔下的陈超探长,早已是西方著名侦探邱小龙用英文写的一系列侦探小说,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达百万册。他自己一直在研究的是诗歌写作、翻译和研究。早年翻译过《四个四重奏》 《丽达与天鹅》 《意象派诗选》等。他坚持写诗多年,痴迷于艾略特的研究。当他的诗歌《舞蹈与舞者》和散文《外滩公园》出版时,《上海书评》请他谈谈诗歌、翻译和侦探小说。
《舞蹈与舞者》
《外滩公园》
虽然你现在是畅销小说作家,但你特别喜欢诗歌,你的小说里有很多种诗歌文本。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早期的诗歌写作和翻译经验与你的侦探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裘小龙:,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没有多想。现在想来,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诗歌,但是读它的人不多。如果你在小说里放一些诗,会有更多的人读。这可能受艾略特的影响。除了写诗,他还写诗写剧,但实际上他不如诗。他的初衷是戏剧的观众一定比诗歌的读者多,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扩大诗歌的观众。20世纪80年代诗歌流行后,诗歌尤其未读。我把诗歌放在一个流行的体裁里,尤其是侦探小说的体裁,读者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先用中文写,后来用英文写,但是我写的是中文故事,也就是说我把很多东西都搞混了。不知道能不能有意识的做一些混合实验。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中有诗,比如四大古典小说。虽然我现在写的是英文,写的也不是中国张辉式的小说,但我考虑是否也可以把诗歌融入小说。我喜欢莎士比亚交替使用诗体和散文体的手法。在叙述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同的抒情强度。在高潮时,如果诗歌出现,抒情强度会立刻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歌的用法。中国古典小说通常每章开头一首诗,结尾一首诗,这是一种实践。对我来说,诗歌可以改变叙事节奏,调节抒情强度。有些段落需要抒情。我要么以我的英雄陈督察的名义写一首诗,要么翻译一首诗。选诗文本与小说的情节氛围一致。这可能受艾略特的影响,《荒原》强调互文性。我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想,这些年中国有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乍一看,我们似乎变了很多,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时,我们内心仍然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一首古典诗词能被恰当地引用,就有点像《荒原》中的——拆穿,突然拆穿,揭露真相。
当然,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写诗。我只是在小说中寻找一个满足我愿望的理由。叶芝有一种理论,认为他在中后期的诗歌中经常使用面具。诗中说话的不是自己,而是戴着面具的人。他想象一个角色,并通过这个角色写诗。在小说里写诗的时候,戴着陈探长的面具。他是党员干部,是警察,而我是书生气十足的迂腐之人。我们的身份完全不同。我绝不会经历他在案件中经历的血腥场面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他和我的视角肯定不一样,他写的诗我也不会多写。后来我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出版了一本专题书《陈探长诗选》,作者是陈探长。这种感觉很奇妙。刚开始只是想引用一些诗词来烘托小说氛围,但是国外出版社不让我这么做,因为要交版权费,只好自己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小
说帮助了我的诗歌,我的诗歌也反过来帮助了我的小说。您曾经在某次讲座当中提到,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不同语言文化体系之间的转换,能请您结合实例深入地谈谈吗?
裘小龙:我的小说涉及不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不少年轻读者都不熟悉。一方面,我想把这些事情通过小说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我不可能像写学术论文一样,加好多注释,这样读者是不会看的。我尽量让全球的读者都能够接受,同时又要像王国维说的那样,不“隔”。这是有点难的,但我觉得还值得做。我自己在学校里教过书,有时候向学生解释某种文化特有的东西,的确不容易,除非让他们去啃一本本学术专著。我曾经读过叶维廉翻译的李商隐的诗,注释密密麻麻,比原文多得多。我想,这样未免多此一举,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会被这些注释吓退,真正精通中国文化的读者,直接读原文就可以了,又何必去看英文呢?我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就想尽量用不隔的方法,帮助读者来理解中国文化有些很难翻译的东西。
拿大闸蟹来举一个例子。相关的情节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里蛮重要的,因为陈探长与他的助手之间的关系本来不怎么好,吃了一顿大闸蟹以后才慢慢好了起来,成了好朋友。这里面的背景知识需要向西方读者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闸蟹在上海是很难弄到的,吃顿大闸蟹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我要向西方读者介绍蟹黄、蟹膏是什么东西。这蛮难的,因为好多中国关于美食的词汇英文里都没有。如果把蟹黄、蟹膏直接按字典意思翻成外文,西方的读者产生不了美食的联想,甚至会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我就像艾略特一样,引用了不少诗,比如苏东坡的“但愿有蟹无监酒”,又安排陈探长助手的太太介绍,怎么通过关系才弄到大闸蟹的,最后还引用了《庄子》里“相濡以沫”的典故,写螃蟹以泡沫互相滋润。总之,把各种各样能用的办法全用上去。
西方人对中国人喜欢吃螃蟹的确是很难理解的,哪怕是讲究美食的法国人也不行。有一次我去法国开会,有几个法国的汉学家提到,李渔喜欢美食,写了不少相关文章。那个开会的地方正好产螃蟹。我就告诉这些法国汉学家,李渔为了吃螃蟹会拼命攒钱,说这是他的“买命钱”。他们听了都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螃蟹在法国也算是好东西,但还没有到不吃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说起来可能煞风景,尽管您在《外滩公园: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一开头就引用了史蒂芬·缪克教授的观点,所谓虚构批评,就是“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同时也承认,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字,并非每篇都是虚构批评,而是处在真假有无之间,但是我仍然忍不住想要追问,其中哪些属于您过往所经历的真实,哪些属于您刻意为之的虚构,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您如何划分,而您又是如何想到要去这样做的?
裘小龙:我在《纽约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中国的现实其实比我的小说更离奇(strange)。其实也不光中国,现实生活与虚构故事之间,有时候很难截然划分。拿美国来说,几年前人家说特朗普会选上总统,上台之后又会做这样那样的事,你也会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我倒没有刻意去编造情节,我只是记录而已。
我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几年前,路易威登公司找到我,让我为他们的产品写一篇东西。我当时就说,你们找错人了,第一我从来不用任何路易威登的产品,第二我是写小说的,不是做创意广告的。结果他又给我寄过来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案件:美国芝加哥曾经有人绑架了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把他装在一个路易威登的箱子里面,从旅馆里面运出去,因为绑架者觉得,把人装在这种很贵的奢侈品箱子里,别人肯定不会怀疑。这样我才算有点明白,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从陈探长的角度来写一篇“植入”他们产品的文章,毕竟陈探长在法国还是蛮受欢迎的。我那个出版社跟他们的关系大概也不错,说让我试试看,否则他们有点为难。我觉得这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故事了。
我本来写不出什么的,后来突然想到,国内做佛事的时候会烧纸钱,以前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现在放在做得很精致的纸糊箱子里,而且都是名牌。我就写陈探长跟一个记者一起去参加陈探长助手太太家里的一场佛事,然后,目睹装满冥钞的纸糊路易威登箱子被烧掉。我写的时候本以为他们是不会用的,因为带有太多讽刺意味,比如文章末尾我让记者讲了句话:这一辈子,有这么一个路易威登的箱子装满了钱,也值了。但是法国人很喜欢,说整个办公室都读了,认为写得很传神,说明路易威登的产品在中国深入人心。
这件事情唯一编造的成分,就是我当时不是完全有把握,烧掉的箱子到底是路易威登还是其他某个名牌。烧的时候,我还听到旁边有人在说:钱很多,快点用。这种情节,一旦放到一个短篇小说里面去,是很荒谬的,但的确又是真实的。
那么您的小说呢?这里面有哪些人和事是您的真实经历?
裘小龙:陈探长这个人物,其实最早的原型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同在一个生产组,不算同事,但都在一个街道。我们同一年考上大学,不在一个学校,但是都读英文专业。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去了安全部门。我的好多小说素材,最早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说的。我这个朋友后来发展得也蛮好,但是他内心深处总还有一种想法:我本来应该去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就像我自己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我本来应该去写诗的。这样的人,本身就有一种张力。我喜欢跟他聊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在思考,当初我如果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我会怎么样?
陈探长助手的太太,原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这一代人,我大概属于例外,没去上山下乡,十年之间还学了点外语,不能说完全浪费。我这位朋友十年完全在农村度过,可是她并没有一蹶不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不仅过好自己的日子,还帮助其他人也把日子过好。这些身边的人和事,慢慢地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有评论说,您在小说里对语言的使用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您总是尽量使用各种很鲜活的中国社会的俗语,您怎么看?
裘小龙:之前我去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认识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的太太庄祖宜,她很喜欢我的小说,说我的小说能够很好地把握和传达中国语言的微妙之处。这其实就是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这篇名作里面说的,写作要力求避免陈词滥调(cliche)。之前我在小说里面描写一些新建造的建筑在上海一夜之间到处都是,英语习惯说mushroomup,意思是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而我没有这样写,而是选择了“雨后春笋”这个中文读者习以为常,但西方读者却闻所未闻的表达。我尽量把诸如此类的表达移植到我的小说里面,让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变化是很大。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翻译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翻译privacy这个词,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完全没有“隐私”这个概念,或者说,即便有,但是大家的理解也是贬义的,与西方社会完全不一样。时至今日,年轻人对隐私的理解,已经基本上与西方社会没什么两样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新奇的表达,例如,“被死亡”“被消失”,等等。这些都是我努力捕捉,并且反映在小说里面的东西。
您已经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序言、随笔、访谈)多次回答了同一问题:为什么要创作侦探小说。相比起这个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您自己爱读哪些侦探、推理小说,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和启发……
裘小龙:其实艾略特就挺喜欢侦探小说的,维特根斯坦也特别喜欢。我自己动笔写小说之前,还真读了不少侦探小说。因为美国的图书馆每隔几个月就会拿一批书出来卖。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忘事,从图书馆借了书会忘记,过两天不还就会罚款。我就去买那种两毛五分钱一本的平装本,一买几大箱,放着慢慢看,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还。有个系列我几乎买齐了,就是“马丁·贝克探案系列”(Martin Beck Police Mystery Series),两个瑞典作家写的。那个时候图便宜,只要两毛五分钱嘛,买了就往下看,第一本看的就是《罗丝安娜》(Roseanna)。后来英国和美国出了一本Books to Die for,介绍最有名的侦探悬疑小说,找不同作家来写哪本书对自己的影响最大,我写的就是《罗丝安娜》。
这两个作家是共产党员,属于左派作家,写小说的初衷是揭露瑞典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没想到写出来之后成了畅销书,他们俩反而赚了很多钱。他们的写法跟传统的写法不一样,侧重于对社会的描写。当初我刚读到的时候就在想,小说居然能这么写,以前我老认为侦探小说就应该是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那种写法。我自己其实最开始想写的也不是侦探小说,我1988年底去的美国,1997年才回中国。回来以后,觉得中国变化挺大的,写了一首长诗,叫《堂吉诃德在中国》,可是自己感觉不好,因为要写中国这么大的社会变迁,诗歌好像没那么得心应手——当然,如果我有艾略特写《荒原》那么大的才气,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我想到了写小说,但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自己在美国读过的马丁·贝克系列。我想,他们可以用侦探小说来描写社会,我也可以。侦探小说有一个好处,框架是固定的:一开始总得有具尸体,之后侦探去查案,最后结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把自己想写的内容塞进去。第一本写完以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侦探小说,就寄给出版社,问他们行不行。然后就签了合同,一直往下写,因为出版社老在催。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写起了侦探小说。
说起来,我的出版社编辑一开始也有点吃不准,因为从来没有哪本侦探小说里面有这么多诗歌。唯一的例外是P. D. 詹姆斯(P. D. James),她笔下的侦探达格利什也是个诗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小说里面写过哪怕一首诗,诗人只是侦探的另一个身份。我的编辑和我商量说,除了艾略特涉及版权问题,必须删去,其他你写的诗歌都保留,但是第二本就不能这么写了,要按照传统的套路来。没想到第一本小说出版以后,有读者专门写信给出版社,说喜欢小说里的诗歌。
那么,读者的反馈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裘小龙:我记得有一位国内的读者,在我的第一本侦探小说译成中文以后,在网上写了篇文章,其中提到我。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之后,转给了我。文章大意是说,我以前翻译的艾略特、叶芝,他是认可的,但是我居然会去写侦探小说,这让他很失望。我的朋友还安慰我,让我别生气。我说我一点都不生气,我挺能理解他的想法的,让他失望,我感到愧疚。1988年我拿了奖学金去美国交流,本来是想搜集资料,写一本艾略特评传的。我特意选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来是因为圣路易斯是艾略特的故乡,二来是因为这所大学是他的祖父创办的。后来我因故滞留美国,评传也没有写出来,还改行写起了侦探小说。但是我对艾略特一直是非常着迷的。前两年还差点把他那间老房子买下来。艾略特的父亲是开砖厂的,建这间三层楼的房子,用的都是特制的红砖,很好看,而且很坚固。后来这个想法给我太太“枪毙”了。她说,你对艾略特已经迷得不像话了,要是买了这间房子,搬进去以后你会走火入魔的。现在想想,我还是应该坚持一下的。
最后,想请您谈谈最近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新作。
裘小龙:我正打算出版一部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是关于狄仁杰探案的。我写了这么多本陈探长探案,他一直忙忙碌碌,得不到休息,这一次,我打算安排他到乡下修养,一面修养,一面自己动手写一本侦探小说,而他自己写的这本侦探小说的案情,和他身边发生的案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等于是一出“戏中戏”。陈探长的小说我还没有写完,陈探长要写的小说我已经替他写完了。意大利出版社的编辑说,那好,就先把这本小说出版了吧。6月我会去意大利,出席一些有关这本以陈探长名义写的小说的出版活动。这种写法,似乎其他的侦探小说家还没有采用过,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