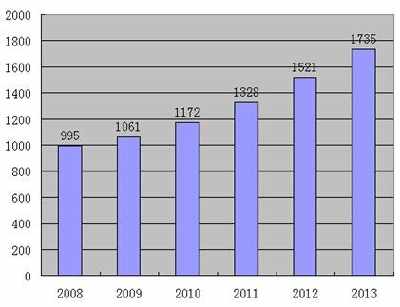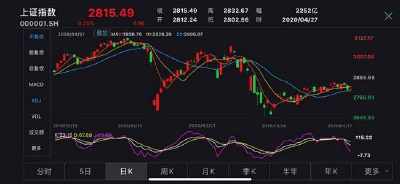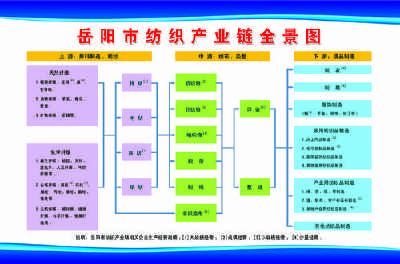一坛陈酒在蔬菜地窖的黑暗中冥想。它是寂静的,带着隐藏的芬芳。它还没有遇到过和你亲近的人,一旦遇到,就会让你感觉很好。
对我父亲来说,那坛老酒是他的心腹。他们彼此不怎么说话,但他们非常关心。那把锄头就是他的头发,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好庄稼。锄头累了,父亲就把锄头的尖端磨得发亮。父亲累了就拿着锄头休息,锄头柄在看太阳,吃着父亲的汗水。父亲的汗水把它喂得又圆又饱。
休息过后,父亲对着锄头喊道:“嗨!老伙计,我们开始工作吧。”我父亲光着青铜背,像另一把锄头一样在阳光下工作。
稻草人,像一个悲伤的孩子。死前服务稻田,死后滋养青山。秋收后能感受到稻草人的孤独吗?
袁野很安静,米粒回到谷仓,鸟儿不常来。稻草人独自站在那里,只有风和他说话。
孤独是一个情感术语,稻草人也无意,所以似乎孤独不能用在上面。然而,我看到的稻草人是孤独的。看着就疼,想抱抱。
我看着它,它充满了心。
没人知道,其实稻草人也有骨头,它的骨头就是它的孤独。
一条路扑向对面的山,躺在那里像一条长蛇吐着信息。它也像村民的扁担。这种极其柔韧的骨头可以从肩膀上卸下来,铺在地上,这样就可以把人从这座山送到那座山。
我知道,在农村,除了我父亲的喉咙,还有一种东西正在变得嘶哑。比如,窗外的山风,就像一个赤脚医生在赶路,紧张地推开木门。不管是寒潮来了,还是春天来了,都是慌慌张张的,很像村里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倔强又老实的骨头,不分青红皂白的报了喜,或者闹出了祸。
深秋的夜晚,在石墩上,几个老人抽着烟,火光随着他们的情绪摇曳着。一个说玉米价格又涨了,明年稻田就要改成旱田了。还有一个说,一半以上的西瓜没买到,烂在地里了。明年我会在城里给人们看大门,我不会种这种狗屎。
农民的可爱之处在于,无论秋收时说了多少狠话,还是要把鹤嘴锄抱在怀里,仔细打磨,让它像身体里倔强的骨头一样闪闪发光,能挖出任何僵硬的泥土。但毕竟父亲年纪大了,眼睛又穷,田里的田埂一点都不直。“我年轻的时候.唉!”他叹了口气,扶了扶腰,却无法摆正悲伤的曲线。
李老栓总是急于告诉村里的后进生正确的装车码垛方式,让他们省下两趟车的油钱和一顿饭的时间。爸爸王喜欢不遗余力地从市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然后空手从那一头走回这一头。他讨厌小偷,他说他看到小偷就想暴打一顿。李老五是个不错的磨刀器。无论是菜刀、镰刀还是猪刀,都能磨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刀刃。每年年底,他家门前的案板上都要磨一堆刀。老婆总会抱怨,她怎么能白指挥别人?他喊道:“一点点帮助有什么用?这只是实力问题!”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今天就用完,睡觉,明天再来。"
在农村,我知道很多中药都改了名字。叶秋叫童拳,铃兰叫香水花,车前的奶名是毛茛,半枝莲的名字是急解,黑泡的民间名字是盖盒,芡实的另一个名字是长刺鸡头芽.这就像二宝现在叫老师,黑蛋叫老板,绑柱叫院长,只是为了换一种药。但我知道他们的骨头没有变,依然和以前一样坚韧。
(作者:朱成玉《人民周刊》 2021年第1期)